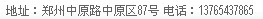|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支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我于年毕业后,去了社区工作了三年。一方面迫于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北京户口,尽管是万分的不愿意,但也还是接受了那个现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人生的经历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改变。可原本是讲解条文,为什么要说曾经的工作经历呢?因为在社区工作的那几年碰到了不少多汗症的患者,而以我当时的认知,只是将仅会的三五个止汗方轮流祭起,结果必然是疗效惨到让我怀疑人生。而这几个仅会的方子里就包括桂枝加附子汤…… 那个时候对于桂枝加附子汤的应用标准很模糊,几乎就是以“大汗出、恶风,小便不利、手足拘紧”这样条文中的症状为标准,没有深究过其病机,可悲的是也从没想过去分析其病机,只是单纯的认为符合经文的必然可行。 然而来就诊的多汗患者恰好满足于这几个症状的几乎是没有,于是我就退而求此次,能满足大部分症状的就用此方,所以结果就是取效者甚微。 实践得到的事实如此,那么条文的价值在哪里呢?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字面上理解条文,而是要从字面分析其病机,这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具体到此条,该如何解? 太阳病,本当发汗。如果发汗得当,汗出证解。汗不够则病不解,汗过则病为之变。此条所讲便是发汗太过引起的坏证。那么这个坏证都有那些呢?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发汗太过可能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只有知道了后果才能分析其机理从而论治。 汗出最直接的是导致津液的丢失,从而津伤生燥。汗出太过,往往外邪已去,此时津液多有丢失,轻者口中不和,可以饮和之。饮就是大米汤,能生补津液,桂枝汤将息法里喝稀粥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临床也多用此法。凡可能汗出太过而伤津液者,令自行多饮米汤而解。重者,虽外邪已去,然而津伤而生热,可成白虎汤证。七八年前我曾接诊过一个小儿高热的,初以大青龙汤发汗,汗大出而致府实津伤做热,以承气汤下燥矢粪液颇多,高热立退,翌日复发热,已是津伤而做热,以白虎汤两剂而安。此案便是伤津之重者之治逆。 汗出除了伤津液之外,还有可能伤及气阴。我曾经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有过接触,他们说干活太猛的话,常常身上出汗其实出的是油,出的油大概就是中医所谓的“阴”吧。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往往都是面色暗黑、形瘦的“阴虚”外貌。当然这个只是我从生活经验上的推测,还是应当从条文中去寻找相应的论述。桂枝新加汤证为汗后伤及气阴,气伤重于津伤者,如条文所示“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若是阴伤多于气伤,则是属于小建中汤系了。再若气阴两伤,累及中阳及血,则是炙甘草汤系。此处若是发挥,涉及内容太多,后至各条文自当详解。此处留有伏笔,只为能明白传变途径,对体系有个大致印象。毕竟本篇的重点是在接下来的汗出而伤阳的情况。 汗出而伤阳,其阳气亦有不同。有伤于卫表之阳气者,导致卫表不能收敛,而发漏汗。此便是桂枝加附子汤证。有伤于里阳之根基,导致里阳不安而作悸者,此是桂枝甘草汤证。在此且按下桂枝甘草汤不多言,主要解析桂枝加附子汤。 汗出伤及卫表之阳,导致腠理大卫开泄,汗液不固而漏出,亦尤其不耐风寒。汗液所泄甚多,必然有津伤之患,肌表之津液欲伤,小便则难,而有作痉之势。条文所说“四支微急、难以屈伸”便是作痉之势,毕竟痉病尚未成,仅见“微急”。从疾病的态势来说,便是在太阳中风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卫表阳气的亏损,治疗便是以桂枝汤加附子以和营卫而补卫表阳气。 若是学究分析至此大功已告成,理解到这个程度而谈及临床应用无非就是等着符合这个病症的患者找上门来,我们再将其认出,处方用药便可收功。有这种层次的认知,以及这样的方法论的指导,倒也说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便是我当年在社区工作时应用此方的状态,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提举一反三、灵活运用了。 桂枝加附子汤证于临床来解,仅知道“漏汗不止、恶风、小便难、四支微急、难以屈伸”尚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了解其流变的过程才能对其治疗有更好的把握。 我们要了解一个证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一来可以在临床上遇到前期状态的时候充分做好预防,防止疾病向前的发展。二来可以预判性的用药,以防疾病流变很快,等到吃上药的时候已经变证而导致用药无效。三者能明白疾病可能引起的潜在趋势,以防解决了是证之后,面对残证而不知从何下手。 以此条为例,具体讲太阳中风证的过汗。 太阳中风证患者本有自汗出,那么汗出多少以及持续的时间就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了。因为汗出多少及持续时间是能影响到此证流变的可能性的因素。新病且汗出不多的,流变可能性小,治疗上仅仅解决是证即可。久病且汗出量较大者,出现流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参照上文所谈到的几点过汗的传变,我们进一步辨证就更有针对性。在治疗上也可以提前做到干预。如汗出量逐渐增大,而恶风寒加重者便可能会往卫表阳虚方向发展,治疗上可加少量附子以防传变。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患者就诊时还是桂枝汤证,就诊取药到家累的一身大汗,药尚未来得及吃,已经就畏寒漏汗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了,此时再吃桂枝汤必然疗效有限。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有所预判,直接给出其变证之方,便会提高疗效。当然,这种难度比较大,若在患者所受影响因素较为单一且医生对疾病发展十分熟悉的前提下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本人就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案例。 上述两种情况或许较难精准完成,但是对残证的处理是必须要熟悉的,因为这种情况太为常见。就桂枝加附子汤本身来说,其治法与所描述的症状是由出入的。仔细看过我上文解析的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提到了此证导致津伤欲成痉病的可能。但是桂枝加附子汤的方药治法却没有顾及津伤痉病!从病机及逻辑上来看,漏汗不止那是必然会导致津液损伤的,且此证的病人也不会在发病第一时间就看病吃药,所以痉病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我在临床不止一次的发现这个问题。桂枝加附子汤的患者就诊,我自信慢慢地开了桂枝加附子汤并告诉患者吃完三副应该就不用复诊了。但是三天后患者还是来了,说吃药特别管用,两副就不出汗不怕冷了,但是现在口干、皮肤痒,想继续调理一下。甚至有的患者明确地说感觉全身肌肉发紧,口中干燥,喝水也难解渴。于是我不得不再重新反思对条文的理解,发现问题就出在对残局没有判断上,津伤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此后我再遇到此类患者时,会根据其病程而酌情加葛根麦冬百合生地等生津之药,即便当下津伤不明显者,我也会嘱咐若喝完药之后出现津伤相关症状须来复诊。有必要多说的是,津伤若不严重,即便是不予生津,稍待时日也能津液自复,若是津伤重了还须治疗。 《伤寒论》中有很多的条文都类似于此,即:给出对当下证的治疗方法,但是当下证治疗完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对残证进行收拾。我在北中医讲座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如今很多的医案一看就是编造的,明明肯定有残证还需要解决的案子,却直接告知治愈。看到这样的案子确实觉得有些尴尬。 到此是发散地说了一些于临床上之指导,但对此条的解析尚有不足,那便是此条于整个体系中位置的意义。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桂枝加附子汤证与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证是太阳病的中风与伤寒欲往少阴病传变的阶段,或者说是太阳少阴合病者。至于其传至少阴后的流变,那就等到后文再说了。 至此该条需要点明的都大致提及。有一些发散的内容等后文再续上了。最后在说明一下,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所说的一些流变情况并没有一一例举,只是挑了部分从常见者解析。 史强多谢各位老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