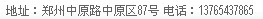|
速康复外科(fast-tracksurgery,FTS)或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recoveryaftersurgery,ERAS)理念丰富了外科学的内涵,外科学从技术到艺术和科学地位突显[1-2]。微创外科技术使快速康复从困惑转化为了现实。研究发现微创外科(腹腔镜外科[3]、胸腔镜外科等[4])手术减少创伤应激反应和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显著缩短住院时间,提高出院后患者的生活质量。ERAS在临床应用中需要多模式或多学科协作完成[2],真正实现从“疾病治疗到健康管理”的转变,这就需要对流程和管理进行优化,目前各个学科只进行局部改进使基于微创技术进步带来的加速康复外科优势打了折扣。因此,基于微创技术对围手术期流程进行优化,理论上应该可以使加速康复外科的优势充分实现。本文结合胸腔镜肺叶切除术(video-assistedthoracicsurgerylobectomy,VATS)围手术期流程优化的实践及国际、国内的新进展,探讨了围手术期流程优化和多学科协作在加速康复外科中的作用。1 术前准备需要完善或优化
术前准备主要是宣教和高危因素评估,必要性如何呢?我们首先分析近年来肺癌外科治疗人群的变化:①早期肺癌(如小结节等),新辅助化疗和二次手术(转移瘤、肺重复癌)患者比例均增加。②高龄(大于65岁)和具有伴随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显著增加。③术前服用药物(如抗凝药、免疫抑制剂或靶向肿瘤药物)且需要肺手术的患者在增加。其次是外科治疗方式的变化:①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已成为主流术式(80%以上),开放手术已成为腔镜手术的补充[5]。②肺段切除比例增加,肺叶切除有所降低,全肺切除显著减少[6]。理论上应该和手术方式同样变化的术前宣传教育、评估体系和高危因素预防治疗却没有发生变化。患者的正确理解与真正的配合治疗,才能使ERAS得以实现[7]。结合快速康复实践发现目前术前宣教中存在以下问题:①护理为主,主要宣传科室情况及注意事项,偏重事务性。②粗略的讲述各专科手术的注意事项,针对性差,可操作性差。③过多术前宣教与准备,增加工作量,因此医患者双方都有走形式的感觉。从深层次看,医患都对术前宣教存在认识的误区,均认为对手术帮助不大(如戒烟),对所有宣教问题的结果如何不清楚。如何才能做到正确的术前宣教并产生好的结果呢?首先护理工作要围绕手术的快速康复进行,并真正理解每一项工作与快速康复的关系,产生“不如此,就如此”的理念,如不戒烟,就增加术后肺部并发症等。其次宣教也要在“群体到个人”“个人到群体”的恰当转换,即群体宣教与个人宣教相结合[7]。最后,医护一体化,并通过项目方式使护士对所从事工作有深入理解,并进行改进,事实证明,这是最好的方式(具体在后详述)。肺癌外科治疗人群和手术方式的变化,寻找合理的术前心、肺功能评估体系和针对高危因素预防治疗方法变得越来越迫切。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exercisetest,CPET)可以弥补静态肺功能检测(restingpulmonaryfunctiontest,PFT)不足,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应用CPET和PFT对例肺癌患者术前检测,提示术前高危因素有[8]:①支气管高反应性;发生率为19.88%(68/);②峰值呼气流量降低(peakexpiratoryflow,PEF)PEFL/min,发生率13.74%(47/);③肺功能处于临界状态(1.0LFEV11.2L,且40%FEV1%60%);④术前吸烟大于年支且戒烟时间小于2周(病史)。⑤术前气管内定植菌存在,且高龄(大于70岁)和吸烟史大于年支的患者[9]。以上高危因素患者进行术前预防治疗:术前的肺康复训练(物理训练)+药物治疗(抗生素、支气管扩张剂和吸入性糖皮质激素),结果表明康复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和肺部感染发生率均较未康复组下降5倍,而康复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显著缩短[8]。进一步研究肺功能差不能手术的肺癌患者进行肺康复训练2周,肺功能可达到肺叶切除术标准,且未增加术后并发症[10]。通过对手术前后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患者心率和动脉血氧饱和度及运动耐力的研究发现,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些研究均提示,现有通过肺功能评估体系进行术前评估肺叶切除的风险已存在局限性,多学科合作(呼吸科或康复科)表明术前评估发现高危因素和预防治疗方法已成为术后肺快速康复的必然[11]。当然这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基于微创肺手术的肺癌患者的适应证可以扩大吗?也就是肺功能标准能够降低吗?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①理论上胸腔镜手术的最大优势在于降低手术创伤对机体的应激,保护了胸廓完整性(保护呼吸肌)和降低疼痛,对肺通气功能影响小且有助于术后排痰,保护了肺功能。②肺手术方式也主要从肺叶切除术向肺段、亚肺叶(二段或三段切除)等,真正最大限度保护肺功能。③合并COPD患者,肺手术后相当于行肺减容手术,有助于改善肺功能。有研究表明肺癌肺叶切除患者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变化幅度(术后第3天同术前FEV1差值)在VATS组(-0.05L)显著低于开胸组(0.19L),相当于节约0.24L肺功能[12],是否可以推测VATS手术肺功能FEV1值可降低0.24L呢?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至少可以提示VATS肺叶切除术肺功能的适应证可扩大。2 手术程序和流程需要优化
“个体化”麻醉应用的必要性:全身麻醉状态下预置各种管道(如:气管内插管、尿管等)的目的是便于手术操作和观察术中脏器情况等,但过多或不必要的管道应用不但增加了术中及术后管理的难度,也给患者带来相应并发症及经济负担。微创手术技术和麻醉技术使手术时间缩短和出血量减少,为术中管道应用优化带来契机。尤其是近年来,不插管(notube)麻醉下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或气管隆突成形术,对肺手术需要全身麻醉的传统观念具有挑战性影响[13]。尽管目前此种麻医院开展,但其观念在快速康复中的应用需要引起重视。全身麻醉气管内插管也有可能将口腔或鼻咽部的致病菌带入到肺部。研究发现气管插管前潄口或清洁口腔,可以显著降低因气管插管导致的口腔或鼻咽部的致病微生物进入下呼吸道,防止肺部感染等[9]。“个体化”麻醉如何在临床上应用呢?①根据手术病种进行“个体化”的麻醉,如非插管全身麻醉下胸腔镜下交感神经烧灼术治疗多汗症或气胸等。②根据手术方式选择麻醉方法,VATS手术时间短,有时可选择非插管、单腔管等。③气管内插管拔管时机也应“个体化”,手术顺利且时间短的患者最好术后立即拔除气管内插管,部分患者可在复苏室拔除,个别需要呼吸机支持的患者才需要到重症监护室拔除。这种统一的麻醉方式和拔管时间,不考虑病种和手术情况的方案,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手术情况是快速康复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手术器械的优化既可以缩短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清点器械时间等)也可以降低费用[14]。事实上,外科手术器械的发展已贯穿整个手术过程,概括起来有切割(电刀)、分离(超声刀)、缝合与止血(切割缝合器、血管夹等)、固定(各种固定器械、机械缝合钉等)。传统应用止血钳和丝线结扎止血的大量器械发挥不了作用,而这些器械仍然出现在器械包里。以胸腔镜肺叶切除器械包为例:开胸器械包72件和腔镜特殊器械26件。临床常用器械进行“模块化”打包后只有11件:能量系统(电刀1把、电钩和超声刀各1),成像系统(镜头和连接线1、穿刺鞘1)和切割与止血系统(双关节钳2把、吸引器1把、止血钳3把和钛夹钳1把);实行“模块化”打包后,清点器械时间、清冼器械时间、安装与拆卸时间和手术总时间均显著缩短,而器械使用率从14%提高到94%[15]。可见,根据病种和手术方式选择合适器械包,不但可以提高效率,也能够降低成本。关键是可以降低术中不良事件发生,缩短手术时间。管道(尿管与引流管)管理也应进行优化。全身麻醉手术常规导尿,目的是监测液体输入和脏器功能。腔镜肺叶切除术时间缩短,需要思考术中常规导尿是否必需?研究表明例肺叶切除术患者平均术中输液量(.10±.67)ml,平均手术时间(2.19±0.44)h,平均术中尿量(.86±.32)ml,这个尿量完全没必要导尿[16]。而麻醉苏醒后诉尿道刺激、苏醒期躁动发生率在导尿组(13.24%,26.47%)均显著高于未导尿组(3.08%,10.77%)(P=0.,P=0.),术后尿潴留导尿组(10.77%)与未导尿组(4.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而术后尿道感染在未导尿组(9.23%)显著低于导尿组(26.4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这个研究回答了并非所有的患者都必需留置尿管,无尿管留置患者术前和术后进行宣教并辅以诱导性排尿,并没有增加术后尿潴留。问题是那些患者需要留置尿管呢?我们基于临床上术中未留置尿管而术后需要再次置尿管的患者分析发现:高龄和前列腺重度增生患者、尿道手术史的患者,手术时间长于4h患者是高危因素(这部分结果随后发表)。胸腔引流管的应用近年来的优化应用也有利于术后快速康复。具体表现在①单管引流取代双管引流(只有脓胸或术中肺漏气严重才考虑用双引流管),单管置于胸顶并应用侧孔,有利于患者术后运动、降低疼痛并提高住院舒适度[17]。②引流管管径变小,尽管尚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16F引流管的引流效果等同于28F~32F且不影响切口愈合[18]。③术后引流管的拔除也不拘泥于一定要少于50~ml/d,而是若无漏气,ml/d也可拔除[19]。④也有术后不应用引流管的报道[20],但是需要术后排气,多数只是术后确认无气体漏出后,马上拔掉,但是需要选择病例且严密监测,目前不能推广,尚需研究。3 术后管理需要优化的方面
外科术后的充分镇疼是快速康复的“nopain或painfree”一部分,这点是共识。外科医生在临床应用中存在问题有:①镇痛不充分或过度,认为止痛药有副反应,而让患者能忍就忍,反之亦然。②用药单一,吗啡类药物应用过多,直接后果是胃肠道反应多。③疼痛评估体系与方法主观性强,导致用药合理性差,缺乏围手术期统筹安排。鉴于以上问题,研究表明,麻醉师或疼痛专业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立足于围手术期疼痛管理,不但有效镇疼,且降低因疼痛导致的并发症。如围手术期合理应用甾体类止痛药同样可以达到吗啡类药的效果,且显著降低恶心、呕吐反应[21]。因此,止痛药应用的合理优化,需要进行研究。当然术后疼痛的原因除了手术本身创伤外,也和术后过多的监测相关。减少不必要监测并优化也有助于缓解疼痛,结合目前胸外科肺叶切除术的特点,具体优化措施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①患者从麻醉复苏室回病房后,是否仍有必要应用心电监护,这极大的限制了患者活动。②尿管应尽早拔掉,强调术前宣教并应用诱导等方法尽量避免重新导尿,若有前列腺增生可考虑应用相关药物。③胸腔引流管尽快拔除,研究发现患者24h后,疼痛主要集中在引流管口;若无临床必需应用原因,最好不用观察或稳妥为借口推迟拔管时间[22]。④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并围绕患者活动优化相应临床干预和药物使用。围手术期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更是快速康复的重要部分,如肺栓塞,术前评估,术后早期预防可以使肺栓塞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围手术期肺康复训练可以显著降低术后肺部感染[23]。4 快速肺康复方案持续优化需要加强术后症状随访管理
围手术期快速康复的评价标准目前大多采用平均住院时间或术后住院时间,尽管有争议但目前也没有更合理的评价方法[24]。最近有研究认为应该用术后患者症状恢复到术前状态的时间作为评价是否达到快速康复的标准,这从另一个侧面提示术后症状管理可以有效促进围手术期流程的持续优化并达到患者快速康复的目的。研究发现,胸腔镜与开放肺叶切除术相比较,术后主要症状依次是疲劳、疼痛、气促、失眠、嗜睡,疲劳恢复的时间最长,而腔镜手术的疼痛恢复时间显著短于开放手术(8dvs.18d,P=0.),同时发现术前身体状况差且伴随疾病多是术后疼痛时间延长的主要因素。提示,术后症状管理并发现高危因素并进行预防治疗,不但优化流程也促进患者快速康复[25]。5 多学科协作、医护一体建立“舒适化”病房
快速康复外科的宗旨是外科手术无风险与无痛苦。无风险与无痛苦主要体现在围手术期,让患者不再害怕手术,需要多学科协作与医护一体化管理。建立“舒适化”病房(painandriskfreeward),真正体现“以患者为中心”医疗理念。多学科协作在肺外科主要是康复科(心肺康复专业)、呼吸科(物理治疗师)、麻醉科、疼痛科和中医科。康复科主要是心肺康复专业方向,围绕术前患者心、肺功能评估,及制订合理心肺康复训练方案,以达到降低手术风险与术后并发症的结果。目前心肺康复主要是训练上、下肢和呼吸肌,改善患者通气和排痰为目的,而对肺功能的换气功能影响甚小,因此我们建议对术前肺癌合并中一重度COPD的患者和因肺功能差不能手术的肺癌患者,可通过术前物理康复的基础上加用药物康复,以清理气道、消除气道炎症,改善通气和弥散功能,以达到降低术后痰潴留和肺部感染等并发症[7]。目前药物康复主要应用在特定的高危因素:如高龄和长期吸烟患者易导致致病性气管定植菌(如G+菌或G-菌)存在,这类患者术前需要用敏感抗生素[8];气道高反应患者应术前应用支气管扩张剂或雾化吸入类糖皮质激素[8];另外清洁气道如应用氨溴索等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和肺部相关并发症。麻醉科除了术前评估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外,还应
外科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外科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些新的外科理论和技术随之出现,从而把外科学推向新的高度。外科学每一阶段的前进都有无数医生为之探索和奋斗,加速康复外科无异是本世纪外科学发展的亮点。尽管如此,基于微创外科技术理念的加速康复外科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以下值得思考的问题:①快速康复临床推进最大的难点在于和快速康复流程相关的工作与现今“指南或共识”有冲突,使医务人员的“安全性”难以满足。②微创技术自身发展过快,而围手术管理措施相对滞后;体现在术前或术后管理仍停留在开放手术层面和微创手术的评价标准(手术适应证)仍延用开放手术的标准。③多学科协作模式临床可操作性差,仍有专科局限;过多的专科细节加入使流程变得繁锁而难以执行。④围手术期医护一体化管理仍有局限,缺少实际内容。⑤基于患者术后结果(patient-reportedout鐧界櫕椋庡尰闄?鍖椾含涓撴不鐧界櫆椋庡尰闄㈠摢瀹舵渶濂?
|